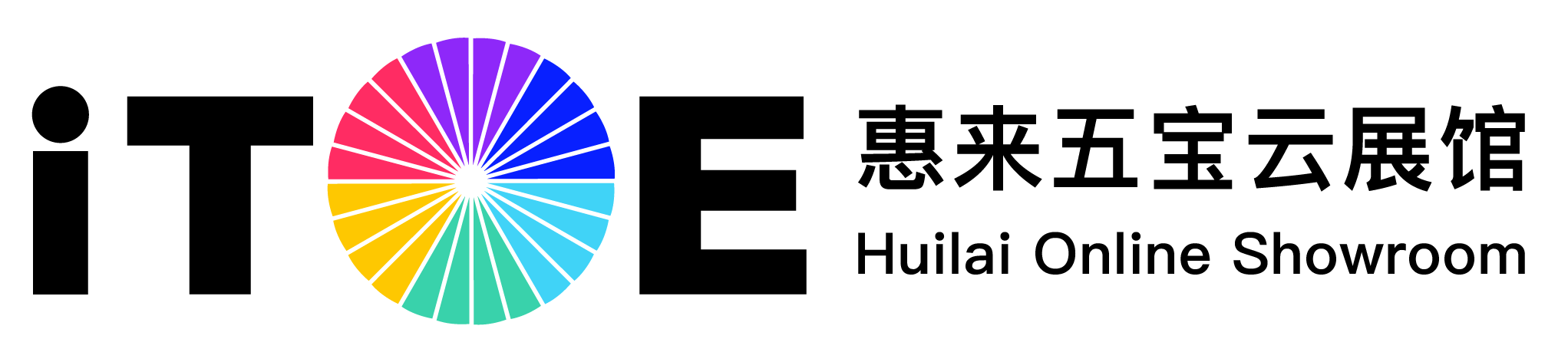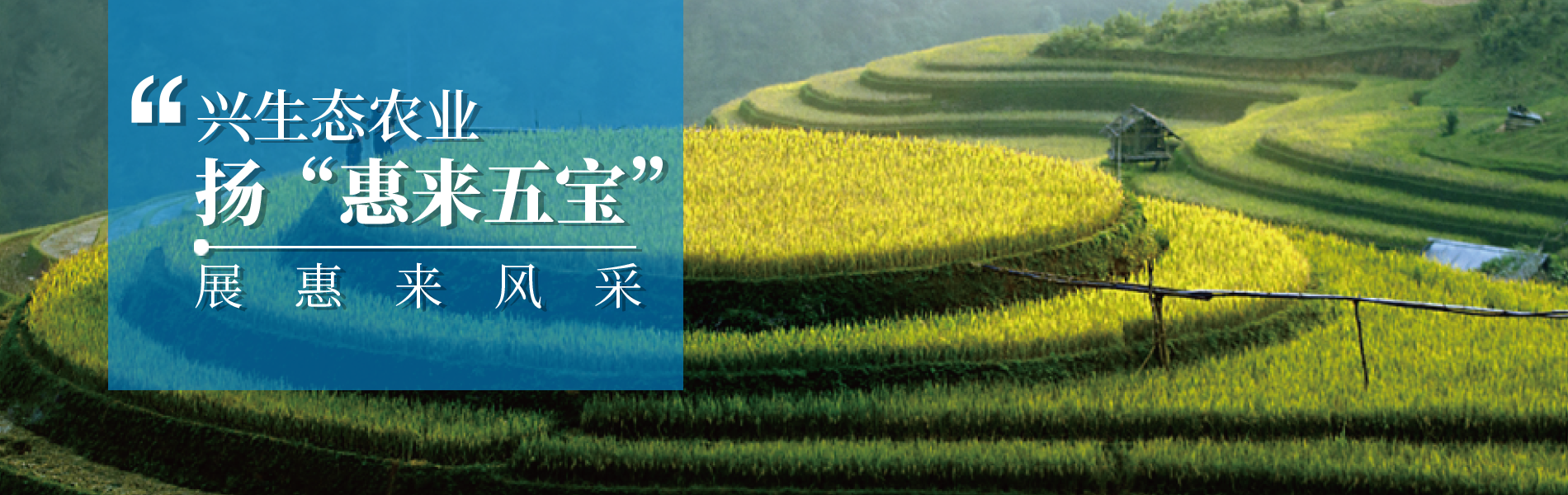
康熙迁界对惠来县的影响
据康熙《惠来县志》记载:“康熙元年壬寅四月,因海氛未息,奉令迁移地亩,勘立边界,将沿海地方斥去三十里,立界设防,令居民移入内地。迁去田地四十三顷四十二亩。自潮阳交界和平寨起,至本县浮埔、靖海所驿后止,建立墩台六所。”
迁界究竟是怎么回事?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为杜绝沿海民众对郑成功军事力量的支援,下令沿海人民迁入内地居住;康熙八年(1669年),因郑军已退守台湾,遂下令展界,各地所展地界幅度不一;康熙十七年(1678年),又因军事需要,再将一些地方的百姓移入原迁界限内;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681~1683年),清廷平定郑军,统一台湾后,才下令全部复界。
康熙元年全国范围的迁界,给整个国家特别是广东、福建等接近台湾的沿海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惠来是当时潮州府的一个滨海小县,不可避免深陷其中。具有民本思想的惠来知县张秉政(康熙十七~二十六年在任),在他主纂的《惠来县志》中,如实记载了这段历史,上面短短的一段文字,潜藏着多少惠来人民的血和泪!
一、原因——“海氛未息”
迁界的唯一原因是抗清的郑成功军事力量对清廷造成威胁,为了隔绝郑成功,而采取这种惨绝人寰的措施。
顺治十三年( 1656年 ),由于郑成功在海边神出鬼没,不时冲击东南沿海,特别是广东、福建一带,清廷颁布“禁海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不但禁止渔船、商船出海捕鱼和贸易,也禁止外来船只进入港口停泊,企图将郑家军困死海上。福建和广东沿海居民首当其冲,很多经济来源断绝,接着殃及到远在南海诸岛谋生的渔人和商贾。
康熙元年(1661)三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登陆台湾,一路所向披靡。清政府急红了眼,悍然采取“根治”手段,于康熙元年(1661)四月,颁布更为彻底也更为残暴的“迁界令”:“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沿海居民被强迫在3日之内搬迁,百姓背井离乡,生灵涂炭。
二、经过——“初迁复迁”
康熙《惠来县志》具体记载了惠来县整个迁界的过程:
“康熙元年壬寅四月,……迁去田地四十三顷四十二亩。”
“二年癸卯八月,知县李济仝大人踏勘绘图,至三年甲辰续迁,共迁去乡村市镇数百处,田地一千六百六十三顷零,随粮男丁一千三百七十四丁,妇女一千七百七十口。”
“四年乙巳春正月,筑建墩台,东北自潮阳交界石坑起,至本县南门外墩止,西南自南门外起,至海丰交界吊旗山止,共计墩台二十九座,墩外剜浚边沟,广五尺,深一丈。”
“六年丁未,筑建营堡,县东建于径口,拨兵四十名守之;县西建于龙江,拨兵百名守之。插竖桩栅四处:惠政桥栅,四间桥栅,林招桥栅,龙江桥栅。”
“八年己酉春二月,展界设防,初迁续迁,一概展复,开垦田地。三年后升科,并撤桩栅,另立边于海口。”
康熙元年(1662)首次迁界,清廷派科尔坤、介推两位大臣负责迁界事宜,从山东至广东,绵长的海岸线所有沿海各处居民一律内迁30~50里,所有沿海船只悉数烧毁,片板不许留存。首次迁界,惠来县“沿海地方斥去三十里”,共迁去田地43顷42亩,占全县可从事农业生产土地的1.76%。当时惠来的海岸线100多里,所迁之地可耕地不多。
康熙三年(1664),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后,清廷气急败坏,再次颁布“迁界令”,这次由伊里布、硕图负责,勒逼广东从饶平、澄海、揭阳、潮阳、惠来至廉江、合浦、钦州等24州县沿海居民再次内迁,并封港毁船,禁止居住。还谕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渔民不准出海捕鱼,出界者立斩不赦。做到彻底“尽夷其地,空其人”。两次迁界,惠来县共迁去土地1663顷,占全县可从事农业生产土地的67.88%;迁移随粮男丁1374人,妇女1770人,共3144人,占全县实在丁口26.56%。惠来县共5都,“迁去大坭、隆井二郡,惠来、酉头、龙溪三都之半”,迁移之地占全县大半。
这还远远不够,清廷还有一系列的“坚壁清野”措施出台:
康熙四年(1665),再次筑墩台,仅一个小小的惠来县,就修筑墩台29座,连同康熙元年所建6座,共35座墩台。墩台外开挖深沟,宽5尺,深1丈。“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劳民伤财。
康熙六年(1667),筑建营堡,于惠来东部建径口堡,守兵40名;于西部建龙江堡,守兵100名。
到处插竖桩栅。惠来县竖栅4处:惠政桥栅,四间桥栅,林招桥栅,龙江桥栅。
沿海迁界的过程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
一是时限紧。按照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
二是放火烧。“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
三是狠心杀。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是一个“杀”字。清廷统治者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迁界之惨酷,诚如屈大均在《 广东新语 》中所写:“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在孙汝谋担任惠来知县(康熙三年~十年)后期,迁界终于有所松动。康熙四年(1665),广东巡抚王来任(有的史料作王来壬)巡视沿海一带,亲见内迁的民众生活十分悲惨,他将实际情况上奏朝廷,希望皇帝能让动迁的百姓回到原来的居住地。康熙七年(1668)春,王来任病故,临终前还向朝廷上奏陈情,恳请展界。康熙八年(1669),朝廷派两广总督周有德前往沿海一带勘察,同年,朝廷恩准惠来展界,但仍然设防,另立边于海口。
后任惠来知县张秉政兴冲冲写下《喜展界》:“万里全疆画界分,于今重复课耕耘。蛟蜃戢影澄遥岛,鸡鹜将雏认里枌。汪泽谕宽三载赋,炊烟缕锁一行云。环郊闻得闹春社,齐颂恩光恰海濆。”
惠来的老百姓为了感谢王来任、周有德两人,遂在靖海、览表、隆江、神泉、资深等地,修建“二公庙”,用隆重的方式纪念巡抚王来任和总督周有德二公。
三、影响——“遍野嗸嗸”
迁界涉及的范围有多远?据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以亿万计”当属文学夸张。在广东,迁界涉及28个州县,深入到田庐连片、农工商业发达地区,被迁士民数百万,抛荒田地共531万亩有余。迁徙之民被迫离开故土,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行乞街市,饿死病死,不计其数。
全面估计迁界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恐怕不可能,仅以惠来县为例。
“遍野嗸嗸”是惠来知县张秉政对于迁界造成影响的沉痛概括。他主纂的康熙二十六年《惠来县志》“贡赋物产”:“惠瘠壤耳,迁移之际,遍野嗸嗸。展界后,哀鸿虽集,而流亡者有之。阡陌虽垦,而汙莱者有之,抚字者亦既心劳矣。”惠来原本就是穷山恶水,迁界期间哀鸿遍野,而展界后,哪怕朝廷“汪泽谕宽三载赋”,百姓仍然困顿不堪,惨淡度日。
综合康熙《潮州府志》和《惠来县志》、雍正《惠来县志》、乾隆《潮州府志》的记载,从顺治十四年(1657)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惠来县人口和农业收入的变化情况如下:
顺治十四年(1657),除“逃、绝、老、幼免编外”,惠来县实编男妇14985人,其中成丁男子6231人,“实在食盐课银” (女人口)8754人。田地、山塘、埔溪2493顷99亩,夏税农桑米75石5斗5升,秋粮米11365石5斗1升。
顺治十七年(1660),惠来县总人口21211人(包括老幼),其中男子11857人。
康熙元年(1662),首次迁界,惠来县迁移43顷42亩,剩下2450顷57亩,实际收成米11281石5斗8升。
康熙三年(1664),第二次迁界后,全县实在男丁4857人,女人口6984人。
康熙十一年(1672),实在男丁5264人,女人口7478人。实在田地、山塘、埔溪1535顷10亩,实际收成米6220石3斗6升。
康熙二十二年(1683),实在男丁5542人,女人口7806人。田地、山塘、埔溪1706顷66亩,实际收成米7078石。
康熙二十五年(1686),实在男子成丁6093人,女人口8505人。
康熙治下,尤其到了中后期,国力日渐强盛,但惠来的经济却沉疴难起,人口增长缓慢,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后,很长时间无法复苏。一直到乾隆年间,才缓和过来。周硕勋乾隆二十八年(1763)《潮州府志》:“各县现届编征实在丁口,……惠来县,男丁六千二百三十一丁,妇女八千七百五十四口,实在共一万四千九百八十五丁口。……又乾隆元年起至二十一年止,盛世滋生永不加赋丁口二千九百丁口。”征税人口终于恢复到顺治十四年的水平。同时,全县课税田地2561顷10亩,实际收成米11737石9斗6升,稍微超过顺治十四年的收成。
数字是枯燥的,无法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让我们看看一些相关的资料记载:
“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每处悬一牌,曰:敢出界者斩!”
“越界数步,即行枭首。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
“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墩,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
……
惠来县仅仅是一个缩影,而且是并不典型的缩影,相对于其他迁界时间长达20多年的地区来说,遭受荼毒只有8年的惠来还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即使是“幸运”的惠来,也还是付出整整106年(1657~1763)的时间,才使全县的经济、人口重新回到百年前的原点。这是惠来人民的血泪史,更是中国历史上惨痛的悲剧!
四、结论——否定态度
志书是官修的,很大程度代表了当时政府的立场和观点。对于康熙年间迁界一事,清王朝的官员们是如何评价的呢?引用清代所编修的志书,看看作为“食君俸禄”的朝廷臣子是怎样的态度。清代潮州知府林杭学(康熙十六~二十七年在任)编纂的《潮州府志》对于康熙年间迁界一事的记载和评价——《海潮揭饶惠澄六县迁地之事》:
边海多寇患,屡躏内地。康熙元年,钦差少宰科尔坤、少司马介推,仝平南王尚可喜、将军王国光、沈永忠、提督杨遇明等,巡勘六县。海滨筑小堤为界,令居民迁入堤内,越界者死,而海寇犹滋蔓也。三年,又差冢宰伊里布、少司马硕图,偕藩院、将军、提督等再巡勘。海阳迁去龙溪、上莆、东莆、南桂四都,秋溪、江东、水南三都之半;潮阳迁去直浦、竹山、招收、砂浦、隆井五都,附廓、峡山、举纟東 三都之半;揭阳迁去地美一都,桃山半都;饶平迁去隆眼、宣化、信宁三都;惠来迁去大坭、隆井二郡,惠来、酉头、龙溪三都之半;澄海迁去上外、中外、下外、蓬州、鱷浦、鮀江六都,仅存蘓湾一都,至五年而全县毕裁,设墩台戍卒以守。七年,抚院王来任上复地之疏,督院周有德毅然行之,民始庆甦生。
从周有德“毅然行之”,可以看出他顶着很大的压力,这压力是来自朝廷的。从“民始庆甦生”,我们更可以想象到老百姓听到展界的消息是多么欢欣鼓舞。如果不是之前的迁界多么不得人心,给老百姓造成了惨痛的灾难,又怎么会有如逢大赦的喜庆呢?
既然是不得人心的政府行为,当然会遭到反抗。见诸记载直接抗拒迁界的是碣石的苏利,林杭学《潮州府志》——《王将军潮惠之捷》:
康熙三年奉旨续迁。土弁苏利据碣石弗从,遣其党劫掠潮阳、惠来地方。将军王国光发兵剿之,斩首千余,余党奔溃。寻合,藩院提督兵征利,一鼓而阵诛之,碣石平。
这是站在歌颂王国光的立场来写这件事的,有点语焉不详。苏利“弗从”,给后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究竟为什么“弗从”?我们再看看张秉政组织编写的《惠来县志》——《苏利抗迁之变》:
康熙元年迁地,二年续迁。知县李济同大人履勘绘图,立界剐沟。碣石苏利抗迁,沿海地方分哨据守。其党郑三据龙江,余煌据神泉,陈烟鸿据靖海。三年八月初七日,征南大将军王国光督师由潮达惠,至靖海大塘埔,烟鸿拒,敌授首,遂长驱至邑。初十日,龙江郑三一鼓而歼,神泉余煌奔窜。师由长青与平藩合剿,利出战南塘埠,杀败身死,大师凯旋。
从一个“抗”字,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一些苗头。不论是“弗从”还是“抗拒”,不难看出修志者站在客观的角度记载“抗迁”者的作为,同时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编者对于迁界一事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