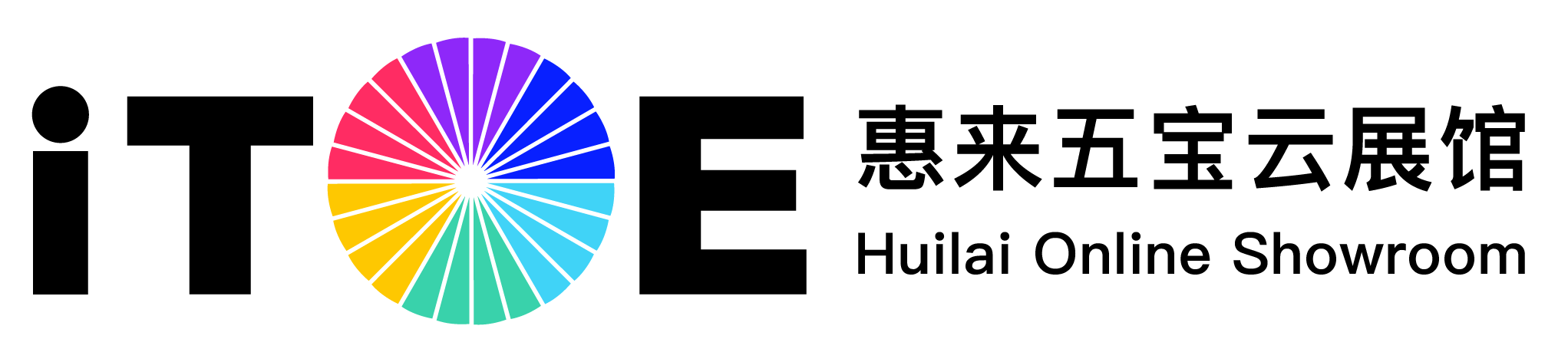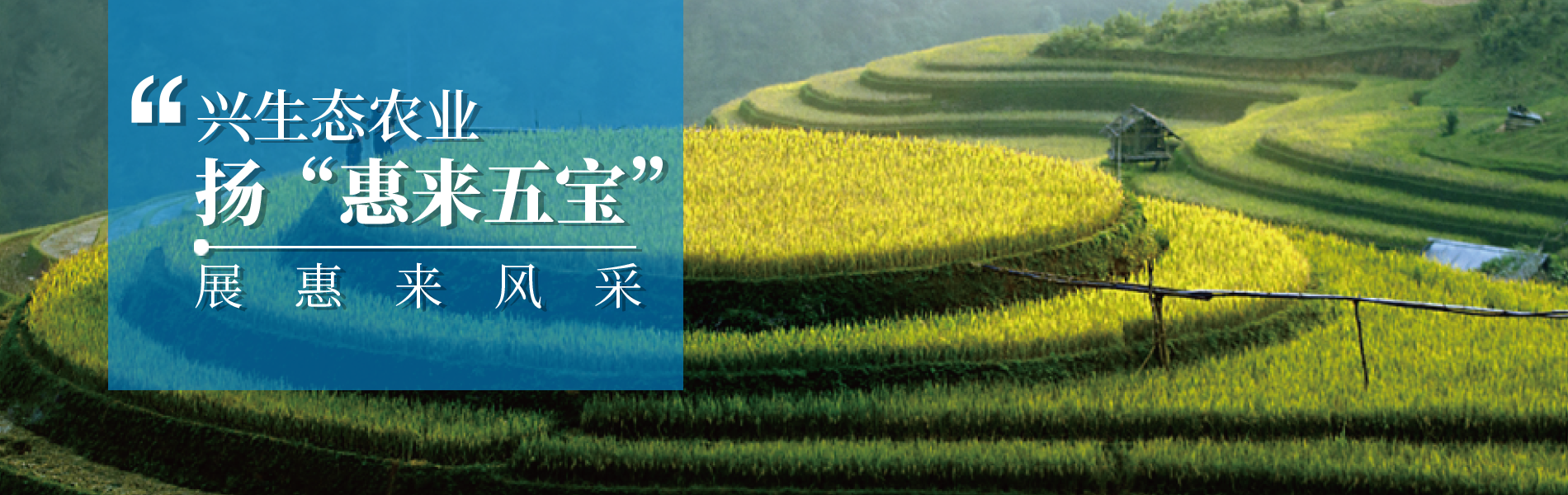
从康熙与雍正年间的《惠来县志》了解惠来 1687年到1731年的44年历史
从文学、影视作品得到的印象,康熙是比较贤明的帝王,而雍正则比较苛厉。但从重修整理、出版的康熙《惠来县志》(下简称《康志》)和雍正《惠来县志》(下简称《雍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反而是雍正年间的经济社会生活好于康熙年间。《康志》的下限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雍志》的下限是雍正九年(1731)。从1687年到1731年,只有44年的时间,惠来和当时的整个社会一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志的史料真实而又细致地反映了44年间惠来方方面面的变化情况,为研究惠来历史提供了一面清晰的镜子。
一、税赋减轻
税赋是衡量封建社会帝王对老百姓剥削程度的一根标尺。
1、人口略有增加。
《康志》:“康熙二十五年,实在男子成丁六千零九十三丁,……妇女八千五百五口。”合共14598人。
《雍志》:“雍正八年,实在男子成丁六千一百二十四丁,……妇女八千六百二十四口。”合共14748人,44年的时间只增加了150人,人口增长比较缓慢。
2、徭役大为减少。
《康志》:“徭役民壮均平共银三千九百六十六两八钱四分七百三毫。”
《雍志》:“雍正八年,实在徭差民壮均平银一千七百五十四两三钱五分七百二毫零,遇闰加银七十四两七钱六分二百零(存为备支)。”即使不计人口增长,徭役负担已经减少了2212两银子。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者逐渐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3、田地税、丁口税减轻。
康熙年间的田地税以粮食计算。《康志》:“康熙二十二年,田地山塘埔溪一千五百三十五顷二纤,续于各年垦复田地山塘一百七十一顷五十五亩九分九厘二毫一丝二忽七微二纤,实在田地山塘溪埔一千七百六顷六十六亩二厘七毫六丝五忽九微四纤,官民夏税农桑米六千二百二十石三斗六升二匀二撮二圭,续于各年垦复官民夏米八百五十七石六斗四升三合三抄三撮五圭八粟五粒,实在官民夏税农桑米七千七十八石三合二勺三抄五撮七圭八粟五粒。”
丁口税以银子计算。《康志》:“妇女丁口共编银八千五百六十三两一钱五分六厘二毫。”
雍正年间的田地税、丁口税是合在一起的。《雍志》:“总计雍正八年丁口田地实征钱粮,……共银一万零二百二十五两八钱四分七厘三毫四丝五忽五微九沙四尘九埃九渺九漠九末,遇闰加银一百八十九两一钱三分四厘六毫零九忽三微一纤零一尘九埃二渺七漠。”
按照丁口税一直没有增加计算,雍正八年的丁口田地税减去康熙年间的丁口税,则雍正八年的田地税实征约1662.69两银子。雍正八年的米价,可以在《雍志》中找到依据:“内除改征本色米价银四百六十六两六钱零六厘七毫六丝四忽四微,折米八百三十一石零四升八合四勺。”即一两银子可以买1.78石米。照此价计算,雍正八年实征田地税,米约2959.59石。与康熙二十二年的7078石减少了4千多石。照此推断,要么是人口税减少,要么是田地税减轻,或者两者都有。
盐税没有变化。两志均载:“盐场有五:平湖、古埕、古丁、神山、惠来。盐课银678两余。”
诚如《雍志》所论:“……国朝正供之外,不加毫末,而蠲免又复频闻,民生其时,抑何幸欤!”雍正年间的税赋,比康熙年间轻多了。
二、科举考试得到大力支持
在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是一件大事。雍正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日趋安定,科举更为得到重视和支持。
年间和年间,从康熙到雍正,县学在经费收入方面有所增加。《康志》记载,康熙年间学校的收入有“学田、学山、学地、学店、文昌阁田、文昌阁铺”。而《雍志》则增加了“俸宾兴田”,可见收入增加了。《雍志》:“俸宾兴田在周田,土名大山、牛路岭等处,一十七石;神泉山等处三石八斗,佃赖衍兴、赖上兴按此田。海丰知县白章署县事,捐俸买酉头都田二十三亩三分,立户‘俸宾兴’。在龙溪都,唐尧恭排内田送儒学,为士子宾兴之资。劂后归县,岁饬仓房,征收宾兴之礼,或行或废,及本府同知张瑗摄县事,择诸生岁董其事,所收租谷,逢大比,在明伦堂举行宾兴,为盛事云。”收入增加了,每逢“大比”之年,即举行盛典,是当时惠来的一件大事。
儒学教谕、训导的薪俸:“儒学教谕、训导二官,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除额荒外),尚实支银二十九两八钱八分五厘零,逢闰加银一两七钱零三厘。”和典史、葵潭巡检司、北山驿驿丞的薪俸一样,比知县“四十五两内(除额荒外),尚实支银四十二两六钱六分五厘零,逢闰加俸银二两三钱二分四厘零”,少了11两多,差距不是很大。
雍正年间廪生的补助也相当不错。《雍志》:“廪生饩粮四十八两(除额荒外),尚实支银四十五两五钱一分零。”供养廪生的费用已经超过知县的工资。《雍志·卷之八·学校》点明当时廪生的人数:“额定廪生二十名,增生如之,附生无定额。”而康熙年间,则只有:“年积银二十五两四钱四分为通学诸生科举路费。”(《康志》)
更为突出的是,《雍志》记载了当时对孔子后代的优厚待遇。《卷之八·圣裔履历》:“……至五十九代孙彦,徙居惠来县大坭都仙塘里及县城关厢、武宁地方,给袭衣顶祀,生四名:孔传隆、孔之时、孔继周、孔广爱。在本学,文庙骏奔,援例呈请宪批,允孔姓优免差役,勒石学宫。”
三、从祭祀方面的情况,也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祠庙增加。在两志《卷之九·秩祀》中,“先师庙、启圣祠、名宦祠”等《康志》介绍的祠庙,《雍志》都有介绍。而《雍志》则增加了“关帝三代祠、双忠庙、忠义孝弟祠、孝节祠”。从名称来看,当时民间百姓对于忠义、孝节的推崇大为盛行。
其次是规模更大。单单举先师庙为例,雍正年间的先师庙绝对超过了康熙年间。雍正年间的先师庙增加了“正殿、四配”,十哲的名字(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冉耕、宰予、冉求、官偃、颛孙师)分列殿内次东、次西两旁。这些变化,可以看出祭拜场所的建设得到加强,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而祭品的变化,更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祭礼更加讲究了。
《康志》:“先师位陈设: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笾八、簠二、簋二、帛一、爵三、豆八。”
《雍志》:“先师正位陈设(遵照雍正三年部颁祭祀器物图):礼神制帛一(白色)、白磁爵三、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二、簋二、笾十、豆十、酒罇一。”
不仅祭器增加白磁爵和酒罇,祭物也增加了牛。不仅正位的陈设有所增加,四配位的陈设、十哲位的陈设同样有所增加。不仅先师庙的陈设更为讲究精细,启圣祠的陈设同样如此,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雍志》还详细地记录了文昌祠、社稷坛、城隍庙、三代关公祠等的陈设,这些内容,都是《康志》所没有的。可见雍正年间祭祀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四、社会更加安定
在两志《建置沿革》中,所记载康熙年间的大事多与军事有关。康熙元年迁界,四年建墩台,六年建营堡,十四年疏浚城壕,二十一年改建墩台5处,三十八年修靖海、神泉二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百姓的徭役能少得了吗?而雍正年间,所记大事已然不同,多与民生、文化、祭祀有关。另外,兵防方面,雍正七年(1729)十二月裁撤北山驿,新设葵潭巡检司。《雍志·卷之一·建置沿革》:“雍正七年,知县张玿美以葵潭乡为闽粤往来孔道,界处崇山,离县甚远,必需专员管理,应设巡检一员,在葵潭驻剳盗贼私枭……”可见当时的葵潭,已成为闽粤交通要道。